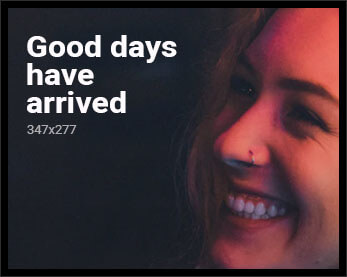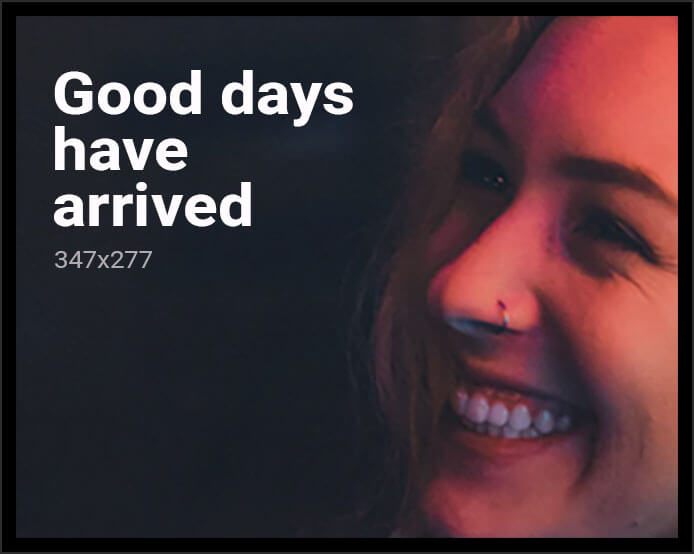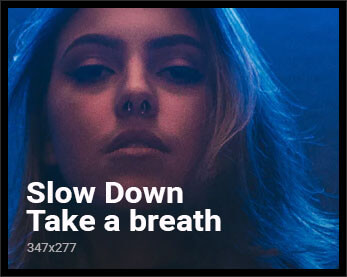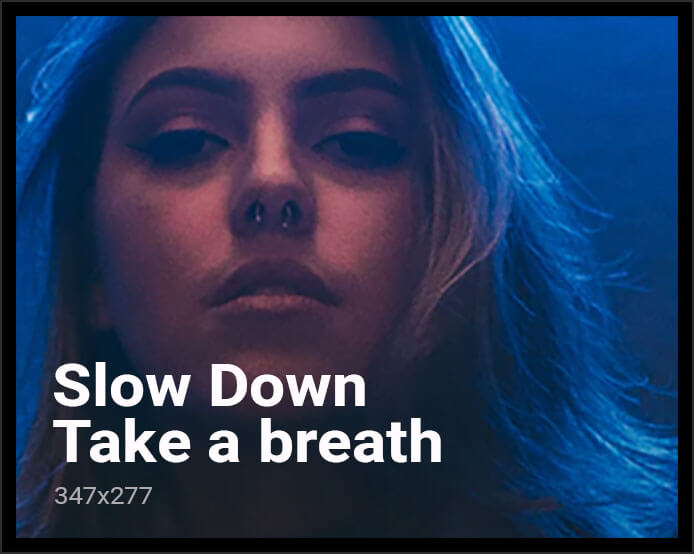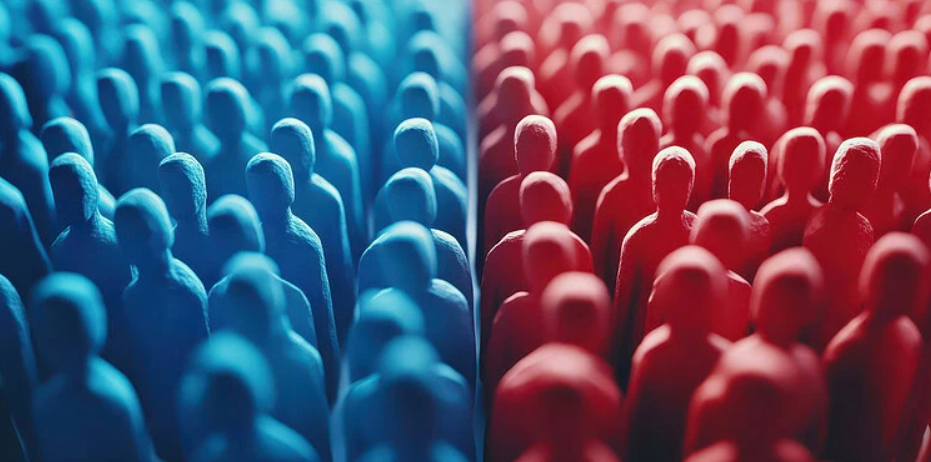
移民、遗产税和大麻合法化有什么共同点?其实没有太多共同点。但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对其中一个问题的立场,我们就能很好地猜测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
政治似乎往往在一个维度上运作:政党和政客位于从极左到极右的光谱中。了解某人对一个尖锐问题的看法通常足以将他们置于这个意识形态维度上,这反过来又使得预测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成为可能。在美国等国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分化为光谱两端的对立政治阵营。
单向度的政治对我们来说就像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自然——这只是我们对政治的看法。但就像引力一样,以这种方式塑造我们的政治的神秘力量确实需要科学的解释。
我和同事们想了解人们为何会如此分裂,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种分裂是如何发生的。该模型表明,我们越无法将政治与个人关系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变得越两极分化。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如果政治被简化为单一的意识形态维度,那么它就会阻碍我们找到解决最紧迫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例如,如果解决住房危机的最佳方案是放松管制和公共投资相结合,那么如果该方案的每一半都被政治派别的一方拒绝,那么该方案可能就无法实施。因此,从非常实际的层面上理解政治如何变得如此两极化非常重要。
问题在于,无论我们回顾过去多久,我们都会发现绝大多数政治都是围绕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主要维度组织起来的: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发生冲突之前,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圆颅党与骑士党之间,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
问题可能已经改变,但基本的二分法仍然保持稳定。这使得调查单向度政治的起源变得非常困难。毕竟,我们无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实验——至少在现实生活中不能。
模拟社会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我们决定采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我们创建了虚拟社会,每个社会都由大量模拟人(称为代理)组成。
每个代理都有各种观点,以多维空间中的坐标表示。我们没有为坐标或维度赋予具体含义,但你可以将它们视为代表不相关的问题,例如国防开支、铁路国有化或堕胎权。
在每次模拟开始时,代理的立场都是完全随机的,并非按照左翼与右翼的单一意识形态维度组织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代理会相互影响,形成新的集体状态。
因此,这些模拟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试验平台,用于检验政治学中使用的不同理论,例如人们是理性的假设,以了解它们是否能够解释单维政治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出现。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将这些理论转化为计算协议,以控制代理的互动以及他们调整意见的方式。然后我们检查这些协议是否足以引发单一意识形态维度的出现。
最初,我们按照主流政治学的传统,将我们的代理人建模为理性的决策者。当遇到其他代理人时,他们要么妥协,要么拒绝,但无论哪种方式,这都不会产生单一的意识形态维度。代理人要么达成共识,要么保持分散。
然而,政治并不是纯粹理性的事情。它往往以直觉和愤怒为特征。但政治学并不总是能成功地将情感融入决策模型。因此,我们向社会心理学的一位创始人寻求灵感。
20 世纪 50 年代,奥地利出生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 (Fritz Heider)创造了“认知平衡理论”这一术语,该理论认为人们力求在思维模式上保持一致。例如,当我们的两个朋友互相憎恨,或者一个朋友爱上我们鄙视的人时,我们会感到不安。同样,我们尽量避免与我们喜欢的人意见不合,就像我们尽量避免与我们不喜欢的人意见一致一样。
我们将这种平衡机制运用到我们的模拟中。当我们的两个智能体相遇时,他们首先确定自己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然后,他们将同意转化为同情,将不同意转化为厌恶。最后,他们调整各自的立场,以增加一致性。
如果他们遇到大多数人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他们就会调整自己的观点来化解剩余的分歧。相反,他们就会试图让自己的分歧变得更加强烈。
每次代理会面时,所有这些都会以微小的增量发生。但通过无数次互动,代理最终会自我组织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维度——无论我们以多少个问题维度开始模拟。
个体行为者最终会在这种意识形态连续体中处于什么位置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问题分歧和个人厌恶之间的联系强度。
如果这种联系很弱——这意味着代理可以彼此不喜欢但仍然同意,或者彼此喜欢但意见不一——代理仍然接近中心。如果这种联系很强,模拟社会就会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它变得两极分化。
这表明两极分化与人们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有关。当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通常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并且怀有良好的意愿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如此多的政治辩论都是通过非个人或匿名社交媒体账户在网上进行的时代,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现实世界比单一的政治观点要复杂得多。人们不仅仅是在网上分享的政治观点。
最终,我们永远无法消除认知平衡的力量——就像我们无法摆脱重力一样。但我们可以找到方法来增进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之间的个人联系。
本文根据知识共享许可从The Conversation转载。阅读原文。